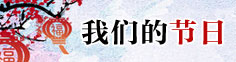文明創(chuàng)建
探義烏民間收藏里的抗戰(zhàn)記憶






當(dāng)指尖拂過(guò)泛黃紙頁(yè),八十多年前的墨跡在陽(yáng)光下蘇醒。
在義烏老物件藏家劉關(guān)良的藏品里,一卷舊刊物上的銳利文字與“抗日自衛(wèi)捐收據(jù)”上的斑駁印章相互映照,共同拼集出一幅全民抗戰(zhàn)的生動(dòng)圖景。如今,這些脆薄的紙張以沉默的方式,訴說(shuō)著烽火歲月里的文化堅(jiān)守與家國(guó)擔(dān)當(dāng)。
舊刊物訴說(shuō)烽火記憶
走進(jìn)劉關(guān)良的書(shū)房,15本泛黃脆薄的《戰(zhàn)地》刊物整齊排列。這些誕生于1940年的出版物,紙張已呈黃褐色,邊角微微卷曲,部分內(nèi)頁(yè)可見(jiàn)蟲(chóng)蛀與水漬痕跡,卻依然清晰記錄著抗戰(zhàn)時(shí)期金華地區(qū)知識(shí)分子的吶喊與熱血。
在一本第六卷第九期的《戰(zhàn)地》封底,幾行豎排字標(biāo)注:“出版者:戰(zhàn)地社,發(fā)行者:戰(zhàn)地服務(wù)團(tuán),金華酒坊巷十一號(hào)”。另一本第六卷第七期內(nèi)頁(yè)印有“東南日?qǐng)?bào)第二印刷廠承印”字樣。據(jù)劉關(guān)良考證,這些刊物正是《東南日?qǐng)?bào)》遷至金華期間出版的。
據(jù)相關(guān)資料顯示,《東南日?qǐng)?bào)》發(fā)行范圍覆蓋浙江、蘇南、閩北、皖南、贛東等地。1937年12月日軍侵占杭州后,報(bào)社遷至浙江省金華縣,1942年受戰(zhàn)局影響,金華版停刊。
據(jù)義烏文史專家傅健介紹,1937年,浙江省政府遷來(lái)金華,金華成了浙江抗日政治、軍事、經(jīng)濟(jì)、文化中心,而酒坊巷則成了浙江的文化中心。除了《浙江潮》外,還有不少新聞通訊社、報(bào)刊遷來(lái)金華,包括《東南日?qǐng)?bào)》《新青年》等。劉關(guān)良收藏的15本出自金華酒坊巷十一號(hào)的《戰(zhàn)地》刊物,即當(dāng)時(shí)的歷史見(jiàn)證,它們提供了原始、真實(shí)的歷史細(xì)節(jié),是研究抗戰(zhàn)史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資料。
翻開(kāi)《戰(zhàn)地》內(nèi)頁(yè),尖銳的標(biāo)題與激昂的文字撲面而來(lái):《運(yùn)動(dòng)會(huì)場(chǎng)的血戰(zhàn)》記錄體育賽事中的愛(ài)國(guó)沖突,《論戰(zhàn)地文化工作》探討文藝武器的戰(zhàn)斗價(jià)值。每一篇文字都展示出驚心動(dòng)魄的現(xiàn)場(chǎng),牽動(dòng)著讀者們的心。
與此同時(shí),劉關(guān)良還珍藏了多本抗戰(zhàn)時(shí)期的外省刊物,如《青年月刊》《中學(xué)生戰(zhàn)時(shí)半月刊》《江西青年》《文藝青年》等,不同刊物都表現(xiàn)出一代青年的精神抉擇。
在一疊刊物中,幾張手抄曲譜尤為特別。工整的五線譜旁,《午飯歌》的歌詞溫暖質(zhì)樸:“先生同學(xué)在一塊,非常的親愛(ài),要吃午飯去了,于是只好離開(kāi)……一天容易過(guò),夕陽(yáng)又西下,鈴聲報(bào)放學(xué),歡天喜地各回家。日日歡敘,暫別只一夜,先生們?cè)贂?huì)吧,小朋友再會(huì)吧。光陰真快呀,又是一周了。小朋友你們的身體強(qiáng)健嗎,學(xué)問(wèn)增進(jìn)嗎,品行端正嗎,小朋友快努力,小朋友快努力。”這些創(chuàng)作于烽火年代的校園歌曲,既是對(duì)和平生活的向往,也是對(duì)文化傳承的堅(jiān)守。
“這些紙張不僅承載著歷史,更延續(xù)著民族精神。”劉關(guān)良說(shuō)道。此刻,午后的陽(yáng)光照在斑駁的紙頁(yè)上,仿佛為那些并未褪色的文字鍍上了金邊。
老收據(jù)彰顯家國(guó)情懷
在劉關(guān)良的藏品中,兩張泛黃脆化的紙質(zhì)收據(jù)靜靜陳列。展開(kāi)其中一張1938年的“抗日自衛(wèi)捐收據(jù)”,豎排右書(shū)的格式、深淺不一的墨跡,以及邊緣處依稀可辨的騎縫章,無(wú)聲訴說(shuō)著那個(gè)烽火連天的歲月往事。
這兩張分別開(kāi)具于1938年11月與1939年12月的“抗日自衛(wèi)捐收據(jù)”,格式高度統(tǒng)一:正文為“今收到( )抗日自衛(wèi)捐國(guó)幣( )元( )角除填繳核存根備查外合給收據(jù)為憑”,落款“義烏縣政府”及經(jīng)收人私章。另一組“自衛(wèi)谷收據(jù)”則采用實(shí)物征收記錄方式,票面標(biāo)注“茲據(jù)( )鄉(xiāng)鎮(zhèn)第( )保第( )甲住戶( )繳納二十八年份自衛(wèi)谷( )市斤已如數(shù)收訖合給此證”,末有經(jīng)手收谷人保長(zhǎng)簽字,票面蓋有騎縫公章。
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幾份印有義西經(jīng)委會(huì)辦事處主任吳山民、副主任楊廣平簽名的支付通知書(shū)。這些姓名在義烏抗戰(zhàn)史上具有特殊意義——吳山民作為統(tǒng)戰(zhàn)代表人物,其簽名票據(jù)成為國(guó)共合作抗日的重要物證。
顧名思義,“抗日自衛(wèi)捐”和“自衛(wèi)谷”,均是供給抗戰(zhàn)軍需之用,是一種地方捐稅。據(jù)義烏叢書(shū)系列之《義烏舊票證》記載,當(dāng)年,凡舉辦事業(yè)和應(yīng)付額外開(kāi)支以及上級(jí)派定的臨時(shí)差辦經(jīng)費(fèi),縣政府大多以開(kāi)征雜捐、加征附加及攤派等來(lái)解決,例如“抗日自衛(wèi)捐”以及“自衛(wèi)谷”等。1937年7月,全面抗戰(zhàn)爆發(fā),各地紛紛組織自衛(wèi)隊(duì)進(jìn)行抗日自衛(wèi),大片國(guó)土淪陷致使政府財(cái)政收入劇減。為了平衡財(cái)政收支,增加財(cái)政收入,增強(qiáng)抗戰(zhàn)力量,全國(guó)實(shí)施了一系列財(cái)政金融改革。
《義烏財(cái)稅志》明確記載,1938年,義烏縣政府尚未繳足“救國(guó)公債款”認(rèn)購(gòu)額的半數(shù)者籌募“自衛(wèi)捐款”,次年改名為“抗日自衛(wèi)事業(yè)費(fèi)”,按上年派額增加三分之二,兩年共募收8.2萬(wàn)元。1940年起由省統(tǒng)籌。1942年1月停征。而“自衛(wèi)谷”作為實(shí)物稅種,直接保障了地方抗日武裝的糧食供給。
收藏物件中,還有一份1945年8月的義烏市第三大隊(duì)“自衛(wèi)谷”收據(jù)。經(jīng)《義烏抗日戰(zhàn)爭(zhēng)史》考證,該部隊(duì)前身正是中共領(lǐng)導(dǎo)的金東義西抗日自衛(wèi)大隊(duì)(后改編為金蕭支隊(duì)第八大隊(duì))。據(jù)悉,金東義西抗日自衛(wèi)大隊(duì)是抗日戰(zhàn)爭(zhēng)時(shí)期由中國(guó)共產(chǎn)黨領(lǐng)導(dǎo)的抗日武裝力量,在金華、義烏等地開(kāi)展游擊斗爭(zhēng),為抗戰(zhàn)勝利作出重要貢獻(xiàn)。據(jù)《義烏抗日戰(zhàn)爭(zhēng)史》記載,第八大隊(duì)成立于1942年,到1943年,義西聯(lián)防隊(duì)解散,第八大隊(duì)改為第三自衛(wèi)大隊(duì)。“上述的第三大隊(duì)?wèi)?yīng)該就是曾經(jīng)聲名顯赫的第八大隊(duì),這份‘自衛(wèi)谷’收據(jù)應(yīng)該就是供第八大隊(duì)所用。”劉關(guān)良表示。這張手寫(xiě)收據(jù)內(nèi)容完整、印章清晰,成為研究義烏敵后抗日武裝補(bǔ)給體系的關(guān)鍵實(shí)物。
每張票據(jù)的背后,都藏著普通民眾的愛(ài)國(guó)情懷。對(duì)此,傅健認(rèn)為,眾多的票證,反映了當(dāng)時(shí)全民上下一致抗日,有錢(qián)出錢(qián)、有力出力,共赴國(guó)難,生動(dòng)展現(xiàn)了抗戰(zhàn)的生動(dòng)畫(huà)卷。雖然材質(zhì)脆弱,但正是這些粗糙的紙張,承載了最堅(jiān)定的信念,其存在本身就是民族精神不屈的象征。“這些被悉心保存的抗戰(zhàn)紙質(zhì)文物是穿越時(shí)空的信使。它們以其獨(dú)特的真實(shí)性,構(gòu)筑起我們與那段悲壯歷史之間的精神橋梁,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沖擊力,故非常珍貴。”傅健表示。(王佳麗)